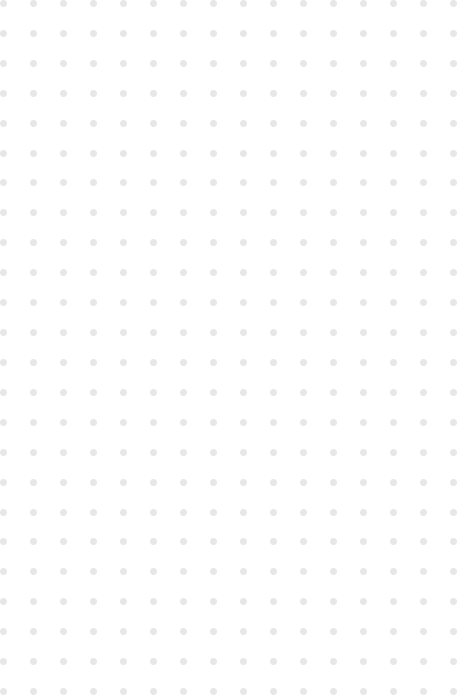1. 醫師回應: 唇顎裂的遺傳屬於多因子遺傳,受多基因與環境因素的影響。事實上,環境因素可能會導致基因突變。目前已知唯一具有自體顯性遺傳模式的基因是IRF6基因,這是一個在唇顎裂研究中相當知名的基因,不僅在人類研究中發現,動物實驗(如小鼠研究)也常以此基因進行相關研究,因此我們也透過這個基因來探討其上下游影響的基因。 今天早上有一位唇裂患童,他的下嘴唇有兩個洞(廔管),這正是IRF6基因突變所導致的Van der Woude(VWS),這是唇顎裂領域中非常有名的syndrome。若患者家族中原本無此病史,但孩子突然發生唇顎裂且伴隨下唇小孔,通常表示此為新生突變所致。由於這是自體顯性遺傳,患者未來若有子女,其下一代遺傳此基因的機率為50%。 除了IRF6基因,目前研究也發現多種可能與唇顎裂相關的基因。現今基因檢測技術相當成熟,如次世代定序(NGS)等方法,可透過抽血分析是否帶有特定基因突變。然而,需注意的是,並非所有帶有這些基因變異的人都會表現出唇顎裂,因為基因的表現受環境因素影響。例如,母親患糖尿病、接受化學治療、吸菸等,都可能增加胎兒發病風險,促使相關基因表達。 目前已知的唇顎裂類型,包括單側或雙側唇裂、單獨的顎裂、唇裂合併顎裂,以及完全或不完全型,其形成與基因表達有密切關聯。然而,除了IRF6基因較為明確外,其它基因的具體表達機制仍在持續研究中。 我們過去曾發表過一些與唇顎裂相關的基因研究。由於這類疾病涉及多基因遺傳,要準確鎖定關鍵基因,通常需要大量的血液樣本,因此國際合作至關重要。例如,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(Johns Hopkins)的一位研究者便與全球多個國家合作,特別是在菲律賓與中國大陸,蒐集患者的血液樣本進行分析。 然而,研究結果顯示,許多基因的臨床表達強度並不明顯,因此我們目前已不再從事相關基因研究。一方面,病人數量減少,另一方面,基因分析的過程相當繁瑣且需投入大量資源。若有需要,醫院仍可提供基因檢測設備與服務,但我的專業重心主要聚焦於外科治療,目前已不再從事基因研究工作。
Copyright © All rights reserved
 厚德醫學講座
厚德醫學講座